

1971年,德国诗人希尔德·多敏获得梅尔斯堡德罗斯特文学奖。多敏的友人、哲学家汉斯·格奥尔格·伽达默尔在颁奖典礼的发言中赋予多敏以“回归诗人”的特殊性。他如此阐释“回归”的意义:“回归不仅仅包含了一位流亡者勇敢而充满冒险的行动,流亡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丧失与告别、异乡与远方、漂泊与暂居、友谊和爱情等经历的总和……她的诗作在谈论我们所有人。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或必须学会什么是回归……希尔德·多敏的诗让我们以新的方式理解什F·么是诗歌。谁若能与她共同认识到回归的意义,就会突然明白,诗总是回归到语言中。”回归与流亡,构成了这位温柔而高寿的女诗人的生平二重奏,也是其大部分作品里反复萦绕的核心母题。
为了进一步阐释她、理解她,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把钥匙,如同挽住她苍老的手掌。接着,奇迹发生了——从诗人的掌心里飞出一只雏鸟,以令人惊讶的姿态飞向高空……没有预告,没有孵化的蛋壳,宛如神谕,却又可以预见。事实上,一切早已揭示:重要的不是祷告,而是接触——在接触的时刻,生命诞生。宛如魔法一般,希尔德·多敏从她自身的笔下逃脱,化为轻盈而有力量的雏鸟飞上天空。而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读者,却仍然沉浸在她的语言所创造出的永恒回响中。

《只有一朵玫瑰支撑——希尔德·多敏诗选》,[德]希尔德·多敏 著,黄雪媛 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在我看来,多敏是个传统主义者。她就像思乡的奥德赛,无论生命的船帆漂流得多远,都不可能抛下爱的港湾和语言的家园。1909年,她出生在科隆。父亲是一名严谨而理性的律师,母亲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声乐家。幼时的多敏衣食无忧,浸泡在家人举办的沙龙活动里,老宅的11个房间永远回荡着欢声笑语。对多敏来说,这是幸福的回声,是充满信任的安乐窝。完整的童年和青春构成无法被时光洗刷的记忆,环绕在诗人周围的保护罩,亦在其生命困顿之时紧紧抵抗着失去的洪流。家人的爱是引她一步步走上正途的指明灯。从科隆女子文理高中毕业后,多敏在海德堡、科隆、柏林学习法律,之后攻读国民经济学、社会学和哲学等学位,并于1931年结识爱人帕姆。1936年,多敏与帕姆成婚,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。在此时,多敏才刚刚扬起她生命的风帆。或许有人遐想:如果多敏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,以其丰富的知识量能做出多少成就?但我们无须纠结于此——只因爱是一件没有等级的事物,而多敏终其一生都在凭心做出自己的选择。
1934年,多敏随帕姆移居意大利,离开了将被纳粹机器控制的德国。五年后,他们又从法西斯的硝烟逃往不列颠。二战爆发,多敏的犹太身份被贴上死亡的标签。来不及哀伤,他们登上了一条蒸汽船,躲在下层的船舱里——大西洋将他们带到多米尼加共和国,一个遥远的彼岸。逃到世界尽头的多敏终于可以松口气,她站在比她个头还高的甘蔗地里,植物对她说着宽容的语言。后来的多敏将会明白这一流亡对她的意义:她自称“语言的奥德赛”,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的旅行,从母语到非母语的旅行。这一切加上其犹太身份,似乎暗合了《圣经·创世纪》,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: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,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……”这本是犹太流浪的宣言,但此刻,她还只是被动地逃脱。只有在日后,多敏才能借着其诗歌成熟的羽翼,将流亡转变为一种有力的回归。
在多米尼加的14年生活是安顿的,却也暗含着感伤。爱催动着多敏心海底部的地幔,使其时时涌起怀念的波涛。偶尔她也呢喃些句子,向着爱人帕姆或一望无际的大海。“我躺在,/你的臂弯里,亲爱的,/像杏仁核躺在杏仁里”。但在那遥远漫长的海岸线上,却找不到一株故乡的巴旦木。1951年,多敏母亲在英国去世,给了她沉重的一击。过往的生活离她彻底远去,她濒临孤独和自杀的边缘。然而,诗歌拯救了她。正是在痛苦的浇砺中,杏仁树成熟了。诗人希尔德·多敏,诞生在世界的尽头。她用多米尼加的国名来命名自己,以报答这片养育了她的土地。它温柔地怀抱着一个双重无根的孤独者,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在那里,玫瑰难以生长,苹果、小麦、桦树无处扎根,她的精神落在一片阒寂的荒原。
在这极为脆弱的时刻,诗歌出现了。或者说,是德语的现身。作为“最后一个不可改变的家”,作为多敏审美的底色,德语拯救了她的精神荒原。这是一种极富巧合的时运:如果将语言视作一种个人的创造,一种附属品,那么属于多敏的德语一定是极为幸运的。它逃脱了战争的破坏,宣传机器的罪恶渊薮。那些因发不出小舌音就要被杀掉的人,那些一提到就会齿根打颤的名字,都没有在她的噩梦中出现。相反,她在多米尼加被异乡的语言保护得很好,直到她必须站出来为死者发声。“草地用泪汪汪的双眼/看着我”,那被雨水冲刷的树根下埋葬了太多的冤魂,痛苦的欲望如火山一般要报复这个肢裂的社会。多敏是时候行动了:她必须鼓起勇气回到家乡,为死者也为她个人建造一个语言的避难所。如果社会不能为你提供一栋住所,那么语言将为你保留最后的家。

希尔德·多敏(1909—2006)
1954年,多敏和帕姆结束流亡,回到德国故乡。对多敏来说,这一次回归有着特殊的现实含义:她作为一个公民回到了受迫害的集体之中,她所使用的语言是诚实的、简单的、纯粹的、克制的——这并不仅仅是对个人诗风的要求,更是时代的要求。多敏的词语总是那样小而珍贵,犹如重建家园的希望。还记得在多米尼加之时,“第二个”多敏刚刚出生。她放声啼哭,想抓住任何东西都是徒劳,且仍然残留着现世沉痛的记忆:“我出生时,父母都已去世。我的母亲几周前刚去世。”可是小小的多敏总是努力呼唤着,努力用她的嘴唇托住每一个逝去的名字:“你的名字在我唇边,/总是在呼唤的边缘,/不能让它掉落,/你名字的每一滴,/都不能落入尘渊。”对她来说,尘渊就是那遍体鳞伤的人间,无人怜悯也无人托付的被黑暗蚕食的阿鼻地狱。在那里,爱呈现出可怕的缺席。她必须“扛着这盛满的器皿/小心翼翼”,对多敏而言,词语永远是一种略重于生命的现实。她必须许下诺言:“你的名字/它不会这样轻轻的跌落/轻得连白昼都不能碎裂/也不会响亮到/让你听见它的声音。”,如此决绝,带着生命的脆弱和坚韧,不仅是说给自己听,也是说给母亲,说给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德国人。
而这坚韧背后是一种推向极致的温柔。一个极权世界被她排除在诗歌之外,却成为了其诗歌母题的成因:正是这样一个空白的极权世界,将人类挤压得和词语一样渺小,一样无能为力。也正是因为太过渺小,才会尝试用一种新语言,去还原本质意义上的人类。希尔德·多敏被吸附在这片土地上。这片土地生产的不是作物,而是语言。果树、花鸟、巴旦木都用其“原初的言语”与灵魂链接。而多敏的诗歌,作为对这些“原初语言”的回应,在构成自身言说的同时,也构成了对其它语言的回声。由此,其诗歌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复合体,进入了生态系统的一部分。这一生态系统是由诗人审美投射的影像,其运行机理是语法和想象编织的绳梯。多敏必须“和果树谈谈”,因为只有在果树里,她才能找到人类。她是一个创造者,同时也是交谈者、倾听者,是她所属的更美的土地的一部分。
就这样,多敏以其柔和的诗风为战后冷雨淋漓的德国带回了一种新想象,一些对破碎的缝补。她的言说带有高度的公民意识和召唤性,毋宁说是在废墟上引领人们前行。其继承至德语诗歌传统的简单、克制,又因其流亡经历而具有的异质性、自然主义和旧日的质地,使这种语言非常适合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德语。事实上,多敏渴望回到集体之中,将语言的避难所带给更多的民众。一直到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,多敏仍活跃在德国各个城市的作品朗诵会上。她把诗歌诵读会看作是生命活力的源泉,也是她作为诗人的公众使命。

实际上,并不是多敏本人拥有号召力,而是她所创作的“新的德语”具有召唤力;同时这种召唤是双向的,在多敏用诗歌,用言说召唤公众的同时,整个社会也以一种“重建家园”的姿态吸引着多敏。因此,每一次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,都是她重新寄寓自己理想的过程,从此她从孤独走向自由。她也证明了自己的判断:“回归比流亡更加重要。”与其说这是个人生平的总结,不如说是多敏践行的对集体的诺言。在此,她打碎了避难所的边界,将现实意识和语言意识交融成一个新的家园。每个人都应该走入这样的家园,去重新体验获得自由的自我。多敏喜欢读两遍诗,也许它的寓意是这样的:即使是相同的人,相同的语言,在不同的时间点也会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意义。没有往日和明天,只有无数个当下,来用勤劳的双手重建家园,如一次次奋力展翅的雏鸟般,将世界从孤独带向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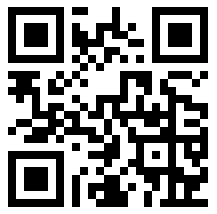
 你正在被职业骗保人围猎!揭开庞大的黑灰产业链|今晚九点半
你正在被职业骗保人围猎!揭开庞大的黑灰产业链|今晚九点半  候鸟 “先遣部队”抵达向海
候鸟 “先遣部队”抵达向海  代表委员在一线|全国人大代表鲁曼:走出一条产业兴村的新路子
代表委员在一线|全国人大代表鲁曼:走出一条产业兴村的新路子  石榴花开映锡林|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:党建引领聚民心 多元共治谱新篇
石榴花开映锡林|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:党建引领聚民心 多元共治谱新篇  快手搜索已全面接入DeepSeek R1
快手搜索已全面接入DeepSeek R1  全省计量技能大比武 “鞍山计量”成绩亮眼
全省计量技能大比武 “鞍山计量”成绩亮眼  防艾走进中学 预防向前延伸 ——新洲区疾控中心开展多病同防健康宣传进校园活动
防艾走进中学 预防向前延伸 ——新洲区疾控中心开展多病同防健康宣传进校园活动  @司机朋友 加油前,这些优惠券记得领!
@司机朋友 加油前,这些优惠券记得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