岭南,五岭之南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释义今广东、广西一带。古人云:五岭者,天地以隔内外。因为峻岭阻隔,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形成了两方天地。在一些古籍中,这里被称为“烟瘴之区”“化外之地”,由此也成为韩愈、苏轼等古代官员的贬谪之处。
然而,从他们的笔记中我们可以发现,他们的流放生活并非全是苦楚。一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似乎改变了很多人对岭南的印象。岭南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地区,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,如海鲜、水果等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岭南与周边地区乃至海外有着密切的交流,促成了兼容并包的饮食文化,从而对粤菜、桂菜等菜系的形成与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,更让美食的繁花绽放至今。
以花煲汤 馥郁芬芳
南宋时期,随着政权的南移,岭南成了士人百姓迁徙的主要地区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动了岭南饮食文化的兴盛,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美食小吃的多样化发展。很多旅居岭南的文人用散文或笔记等方式记录风物美食,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。周去非所著的《岭外代答》就是这样一本“广泛收录、随事笔记”的岭南知识宝典。
周去非是浙江永嘉(今温州)人,曾在广西做过官。他撰写《岭外代答》十卷,条分缕析地揭开了广南西路(今广西全境以及雷州半岛、海南岛等地)的神秘面纱。
在“花木门”中,周去非介绍了当地诸多水果、香料,可谓五花八门,其中有不少关于“药食两用”植物的一手资料,如“荐酒,芬味甚高”的红盐草果、“枝能发散,肉能补益”的桂树。还记载了一些与物产相关的传说故事,据说钦州灵山县有一位宁姓老人,在山间忽然看见遍山的余甘子,这种果子一般是“虽腐尤坚脆”的,但这位老人吃的时候却入口软熟,待他大快朵颐后,余甘子“须臾便复青脆”。老人回乡告知闾里,传为异事。
除自然物产外,周去非还记录了很多饮品。据记载,第一次喝到椰汁的周去非感叹“子中穣白如玉,味美如牛乳,穣中酒新者极清芳”。在静江(今广西桂林),赶路人还喜欢将豆腐羹就着白酒食用,谓之“豆腐酒”。书中还提到岭南人喜食“不乃羹”,这是一种以动物内脏、羊肉、鸡肉等混合熬制的浓汤,味道独特,上菜的时候,肉捞出来弃之不用,只以汤待客。之所以命名为“不乃羹”,意思是说,喝了这道汤,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。
说到饮品,两宋时期岭南的花汤已经远近闻名。岭南人喜欢煲花汤,如“天香汤”“春元汤”“茉莉汤”“甘菊汤”等,都是鲜花唱主角。“百姓爱喝汤,百花来添味”的轶事,给千年岭南花事增添了优雅又不失烟火气的趣味。
宋人喜欢追求精致优雅的生活。在他们看来,赏花与食花都是高品位的体现,以花煎茶、以花煲汤,既不辜负大自然,待客亦有风度。
以花煲汤,自然要给汤取个好名字。所谓“天香汤”,其实就是桂花汤,摘桂花一定要在清晨,一片片带露的花瓣摘下,去掉花蒂、花萼后,放在白瓷瓶中,待积少成多,用新砂盆擂烂成泥,再封在瓷瓶中,等足七日。要喝的时候,加一勺在沸汤中,沁人心脾,此味只应天上有,故而名曰“天香汤”。
以此类推,“春元汤”便是梅花汤,不过,取的是将开未开的花骨朵,预示着春天的开始。最有意思的是“百花汤”,要摘各种香而无毒的花,放在白瓷瓶中,用冷开水浸一宿,瓶口还要密封住,第二天清晨把花撇去,只“汤浸香水”而饮,回味无穷。另外还有“双花饮”,在岭南茶肆中,茶博士以银匙舀取桂花蜜,调入茶汤,再浮一二茉莉,便是“双花饮”。
宋代官府有一项政策,凡是节庆日,官府的园林一律向百姓免费开放。此时,府里的仆人会在园中摆个小食摊,赚些外快。除了茶点,这些小食摊上最惹眼的就是花汤。府中会依照不同的时节,分别煲出“天香汤”“春元汤”“茉莉汤”或“百花汤”等。这些以鲜花为主的美味花汤与以肉为主的“不乃羹”,完全是两种风格。
其实,以花煲汤只是岭南先民热爱鲜花的一种表达,他们食花的方式林林总总,如将各种花瓣制酱、煎炒、凉拌生食、制作花露等。其中,有一种食花之法,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大放异彩,这便是闻名千年的朱槿渍荔枝。
荔枝的美味早在汉代就已为中原人熟知,但运输保鲜是个难题。凭借古人的智慧,朱槿花闪亮登场。人们将朱槿花瓣碾压成泥,拌上一点点盐卤,制成红浆,再以红浆腌渍荔枝,随后细心晒干。以朱槿花腌渍的荔枝干“色红而甘酸”,而且三四年不会生虫,既可从容向朝廷进贡,又可方便客居广州的外商带上船归乡。朱槿是开遍竹篱茅舍边的常见花,荔枝是闻名遐迩的岭南佳果,鲜花与佳果相伴,演绎出一段千古佳话。
琳琅小食 百味纷呈
两宋之际,南迁岭南的中原人口不但带来了中原地区的烹饪技法,也让一些北方小吃“找”到了新的归宿,落户南国,再加上本土的特色小吃,彼时的岭南市井街巷氤氲着糖霜与稻香交织的烟火气。茶寮檐角下、斑驳竹影间,六仙桌上青瓷盏飘着茶烟,藤编食盒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各色精美小吃——这些方寸之间的风物,是山海馈赠的凝华,亦是文人笔下流淌的诗意。
岭南临海,小吃亦染咸潮。南宋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载有美食“蟹酿橙”,取黄熟朱栾(橙子),剜瓤留盏,填蟹膏姜末,蒸熟后“(味)香而鲜,使人有新酒菊花、香橙螃蟹之兴”。这一美食本为江南雅馔,传入岭南后,当地人以青蟹替代湖蟹,添入紫苏、茱萸,橙香与海腥相激,竟成特色肴馔。食客以银匙舀食,谓其“一盏吞尽南海秋”。
更寻常的,是街角老妪兜售的“蚝饼”。生蚝捣泥为酱,混入猪油、麦面,擀作薄片,炭炉烘烤至酥脆。《岭外代答》曾记岭南人制蚝:“肉大者腌为炙,小者炒食。”酥饼承此遗风,佐以荔枝蜜茶,咸鲜透甜,市井小儿常攥铜板争购,称其为“咬得浪花碎”。此外,还有疍家糕和白糍。疍家糕是端州(今广东肇庆)西江水上人家的传统食品,层层相叠,又称为千层糕,有咸、甜两种味道。白糍类似于今天的糍粑,将糯米蒸熟后趁热用杆杵反复捶打成黏性的一团,然后用手按压成饼状。新鲜舂出来的白糍裹上美味的鸡蛋或清蘸酱油、豆粉来吃,味美可口。
岭南果木繁盛,点心亦染荔蜜蕉甜。南宋诗人杨万里过岭南梅州(今广东梅州)时,见集市妇人以蕉叶裹糯米,蒸熟蘸糖霜食用,甚异之。其实,这便是如今岭南著名的小吃“蕉叶糍”,南宋时已成当地节庆必备食品。更有“荔枝红糕”,取荔枝果肉捣泥,与粳米粉同蒸,点以玫瑰露,被当时文人赞其“色如晚霞,甜不掩果香”。
七宝擂茶是一种混合了多种食材如芝麻、绿豆、葛粉、糯米、红豆、生姜等的养生茶饮。擂者,研磨也。擂茶就是把茶叶、芝麻、红豆等原料放进擂钵里研磨后再冲水喝,其似茶非茶、似粥非粥、似饭非饭,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味道。结合“捣烂成糊状,冲开水和匀”的制作方法,七宝擂茶和八宝粥在味道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。
考古发现,七宝擂茶始于五代,流行于宋代。两宋之际,为了躲避战乱,大批客家人自中原向南迁徙。他们在中原地区就有饮茗茶、食茗粥的习惯,南迁过程中又曾长时间滞留于茗粥盛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,擂茶习俗被不断丰富。最终,客家人迁至岭南、福建以及赣南地区。在这些地区,新迁入的客家人占有文化优势,擂茶习俗被完整地保留下来,并不断被发扬光大。
煎堆是糯米粉通过油炸再沾满芝麻的一种点心,也称麻团。在如今岭南广大乡村,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煎堆。“煎堆碌碌,金银满屋”,其属于节庆婚礼等喜庆食品。史料记载,煎堆的前身名叫煎、焦。
是一种以球形丸状为主要特征或蒸或炸的粉制点心,而在宋代,大多指球状油炸品,并且有一个常见的称呼——焦。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“唯焦以竹架子出青伞上,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,架子前后亦设灯笼,敲鼓应拍,团团转走,谓之‘打旋罗’,街巷处处有之。”南宋末年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写道:“京师上元节,食焦,最盛且久,又大者名柏头焦。凡卖,必鸣鼓,谓之‘鼓’。每以竹架子出青伞,缀装梅红缕金小灯球儿,竹架前后,亦设灯笼。敲鼓应拍,团团转走,谓之‘打旋’。罗列街巷,处处有之。”《岁时广记》像是对《东京梦华录》进行了解释,两本书都详细记载了当时人们食焦的情形。那时焦是元宵节的节令食品,卖焦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,设计了一种名为“打旋罗”的招徕方式。这种招徕方式在北宋都城汴梁的街巷中随处可见。
南宋时期,食用焦的习惯在岭南地区得以延续,只是名称逐渐演变成煎堆。岭南人还给煎堆赋予了吉祥寓意,油、糖、谷花、芝麻象征人丁兴旺、生活甜蜜、节节高升,比较出名的有广东佛山的龙江煎堆、九江煎堆和广东中山的爆谷煎堆。作为昔日北宋都城著名小吃之一的焦,如今早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大众美食。
虾酱饭是一道源于岭南地区的经典家常美食,浓郁鲜香,其体现了粤菜讲究食材原味的烹饪哲学。
作为虾酱饭的核心调料,虾酱以新鲜小虾或虾米发酵制成,在岭南地区特别是珠三角一带广泛流行。虾酱历史悠久,据史书记载,其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。宋人赵汝适在《诸蕃志》中提到过“虾羹”,即虾酱的雏形。作为一道简单却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,虾酱饭既体现了岭南人注重调味的烹饪传统,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将平凡食材幻化为传奇美味的智慧。
(王宁 综合整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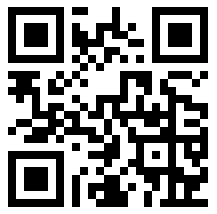
 你正在被职业骗保人围猎!揭开庞大的黑灰产业链|今晚九点半
你正在被职业骗保人围猎!揭开庞大的黑灰产业链|今晚九点半  候鸟 “先遣部队”抵达向海
候鸟 “先遣部队”抵达向海  代表委员在一线|全国人大代表鲁曼:走出一条产业兴村的新路子
代表委员在一线|全国人大代表鲁曼:走出一条产业兴村的新路子  石榴花开映锡林|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:党建引领聚民心 多元共治谱新篇
石榴花开映锡林|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:党建引领聚民心 多元共治谱新篇  快手搜索已全面接入DeepSeek R1
快手搜索已全面接入DeepSeek R1  全省计量技能大比武 “鞍山计量”成绩亮眼
全省计量技能大比武 “鞍山计量”成绩亮眼  防艾走进中学 预防向前延伸 ——新洲区疾控中心开展多病同防健康宣传进校园活动
防艾走进中学 预防向前延伸 ——新洲区疾控中心开展多病同防健康宣传进校园活动  @司机朋友 加油前,这些优惠券记得领!
@司机朋友 加油前,这些优惠券记得领!